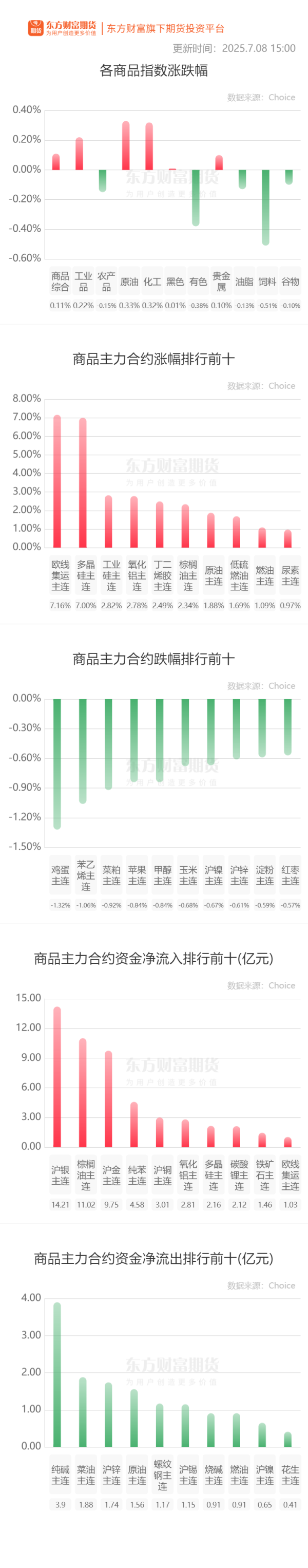《再评唐诗三百首》|论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》:盛衰之镜中的艺术史诗国内正规配资公司
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》
唐·杜甫
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,夔府别驾元持宅,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,壮其蔚跂,问其所师,曰:“余公孙大娘弟子也。” 开元五载,余尚童稚,记于郾城观公孙氏,舞剑器浑脱, 浏漓顿挫,独出冠时,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,洎外供奉舞女, 晓是舞者,圣文神武皇帝初,公孙一人而已。 玉貌锦衣,况余白首,今兹弟子,亦非盛颜。 既辨其由来,知波澜莫二,抚事慷慨,聊为《剑器行》。 昔者吴人张旭,善草书帖,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,自此草书长进,豪荡感激,即公孙可知矣。
昔有佳人公孙氏,一舞剑器动四方。
观者如山色沮丧,天地为之久低昂。
㸌如羿射九日落,矫如群帝骖龙翔。
展开剩余82%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。
绛唇珠袖两寂寞,晚有弟子传芬芳。
临颍美人在白帝,妙舞此曲神扬扬。
与余问答既有以,感时抚事增惋伤。
先帝侍女八千人,公孙剑器初第一。
五十年间似反掌,风尘澒动昏王室。
梨园弟子散如烟,女乐余姿映寒日。
金粟堆前木已拱,瞿唐石城草萧瑟。
玳筵急管曲复终,乐极哀来月东出。
老夫不知其所往,足茧荒山转愁疾。
杜甫以一场跨越五十年的剑器舞为叙事支点,在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》中构建起盛唐气象与中唐衰世的双重镜像。诗序开篇即以"大历二年"与"开元五载"的时间坐标,将个人记忆锚定于历史转折的裂谷之中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不仅是技艺的巅峰,更是盛唐文化繁荣的缩影,其"浏漓顿挫,独出冠时"的舞姿,与玄宗朝"宜春、梨园二伎坊"的制度性支持互为表里,共同铸就了"先帝侍女八千人,公孙剑器初第一"的文化奇观。当诗人于夔州重见李十二娘演绎同一支舞蹈时,昔日的辉煌已如"梨园弟子散如烟",只剩"女乐余姿映寒日"的苍凉剪影。这种今昔对比绝非简单的怀旧,而是通过剑器舞的传承断裂,揭示了安史之乱后"风尘澒动昏王室"的历史必然。公孙大娘从"玉貌锦衣"到"绛唇珠袖两寂寞"的命运轨迹,与杜甫自身"白首""足茧荒山"的漂泊形成互文,将个体生命体验升华为对时代兴衰的哲学思考。
这种艺术与历史的交织不仅体现在主题层面,更深入到思想内涵之中。诗中公孙大娘的剑器舞被赋予双重象征意义:既是"㸌如羿射九日落"的视觉奇观,也是"豪荡感激"的精神图腾。张旭观舞后草书长进的故事,揭示了艺术门类间的通感效应——剑器舞的节奏与力度,通过张旭的笔触转化为书法艺术的张力,印证了盛唐文化"破体为文"的创造性思维。这种跨媒介的艺术互动,使剑器舞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表演,成为盛唐文化创新活力的物质载体。杜甫采用"以小见大"的叙事策略,通过剑器舞的今昔对比,完成对五十年历史变迁的压缩式呈现。"五十年间似反掌"的时空压缩,将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的因果链浓缩于舞蹈的起承转合之中。诗中"金粟堆前木已拱"与"瞿唐石城草萧瑟"的意象并置,既是对玄宗陵墓荒芜的实景描写,也是对盛唐精神陨落的隐喻性表达。这种时空折叠的叙事手法,使诗歌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"历史容器"。诗末"老夫不知其所往,足茧荒山转愁疾"的独白,将历史反思引向存在主义层面。杜甫以"茧足"象征自身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困境,其"转愁疾"的生理反应与"乐极哀来"的心理节奏形成共振,揭示出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困境。这种将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相绑定的书写方式,使诗歌超越了普通怀古诗的范畴,成为对文明衰落过程中人性异化的深刻叩问。
诗歌展现了多重艺术手法的创新性融合。"㸌如羿射九日落""矫如群帝骖龙翔"等"四如句",通过解构传统神话原型,创造了全新的审美体验。后羿射日的典故被转化为剑光如日的视觉冲击,"群帝骖龙"则将天帝巡游的庄严感嫁接到舞者腾跃的姿态上。这种陌生化处理既保留了神话的崇高感,又赋予其现代性的张力,使舞蹈描写突破了具象模仿的局限,达到"象外之象"的审美境界。全诗采用"浏漓顿挫"的声律设计,模拟剑器舞的节奏变化。开篇"昔有佳人公孙氏"以平稳的叙事节奏引入,至"观者如山色沮丧"突然转入激越的抒情,继而通过"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"的急缓对比,完整再现了舞蹈从爆发到收束的全过程。这种以声律模拟舞姿的创作手法,使诗歌本身成为一种"无声的舞蹈",实现了文学与舞蹈的跨艺术对话。杜甫创造性地运用蒙太奇手法,在现实观察与历史记忆间自由切换。诗中既有对李十二娘当下表演的实写("妙舞此曲神扬扬"),也有对公孙大娘往昔风采的虚构("天地为之久低昂"),更有对玄宗朝文化盛况的想象性重构("先帝侍女八千人")。三种时空维度通过"与余问答既有以"的对话场景有机串联,形成多声部的叙事交响,这种结构方式比白居易《琵琶行》的单线叙事更具历史纵深感。
杜甫将剑器舞这一表演艺术纳入"诗史"书写体系,开创了"以舞写史"的独特路径。诗中通过公孙大娘的技艺传承,勾勒出唐代乐舞制度从"梨园精修"到"流散民间"的衰变轨迹,这种微观视角的历史书写,比传统史书的宏观叙事更具人文温度。正如王嗣奭所言:"咏李氏,却思公孙;咏公孙,却思先帝",诗歌通过舞蹈艺术的兴衰,完成了对盛唐文化生态的系统性追忆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被赋予强烈的身体政治学意义。其"戎装执剑"的舞姿,既是对盛唐尚武精神的艺术再现,也是对女性身体力量的诗意礼赞。杜甫通过"矫如群帝骖龙翔"等描写,将舞者的身体动作升华为具有宇宙秩序感的意象,这种对身体美学的深度开掘,使诗歌突破了传统咏舞诗的感官描写层面,进入形而上的哲学思考领域。诗序中提及张旭观舞后草书精进的故事,实质上构建了一个"艺术家-艺术-艺术"的接受美学模型。公孙大娘的舞蹈不仅是表演对象,更成为激发其他艺术家创造力的媒介。这种跨媒介的接受关系,预示了后世艺术理论中"互文性"概念的核心要义。杜甫通过这一设计,将诗歌的接受过程转化为对艺术创造本质的探讨,使作品具有了元诗学的自反性特征。
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》的伟大之处,在于它既是一部盛唐的挽歌,也是一曲文明的安魂曲。杜甫以剑器舞为棱镜,折射出历史变迁中艺术精神的坚守与变异。当"玳筵急管曲复终"的乐声与"月东出"的自然节奏形成和弦,诗歌最终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,成为对人类文明永恒困境的诗意回应。在历史盛衰的轮回里,艺术始终是穿透阴霾的火种,而诗人则是守护这火种的孤独行者。这种将个体命运、艺术传承与历史进程熔铸一炉的创作实践,使杜甫的这首长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可复制的巅峰之作。(本诗评独家首发,选自史传统《再评唐诗三百首》第二辑:七言古诗。本书稿寻求合作出版商)
作者简介:史传统,诗人、评论家,中国国际教育学院(集团)文学院副院长,中国财经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、高级评论员,人民网人民智作认证创作者。著有评论专著《鹤的鸣叫:论周瑟瑟的诗歌》(20万字)、评论集《再评唐诗三百首》(60万字),诗集《九州风物吟》国内正规配资公司,散文集《山河绮梦》、《心湖涟语》。发布各种评论、诗歌、散文作品2000多篇(首),累计500多万字。
发布于:辽宁省富华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